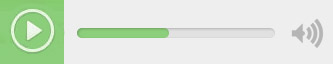西湖浪漫,因為這里曾住過兩條婀娜多姿的美女蛇,大概男人們的心中都有著這樣兩個女子,一個溫婉賢淑,一個嬌俏活潑。
很喜歡“文妖”李碧華的一段話,女人們都渴望遇到兩個男子,一個是許仙,一個是法海。這大抵是因為,許仙愛的癡心,而法海更有征服欲吧!
民國時期,就有這樣一個奇女子,她是魯迅口中“最好的短篇小說家之一”,也是一位徹底的無產階級文學家。也正是這位不凡的女子,竟然開啟了二男一女“三人行”的先河。就在美麗的杭州,她同時擁有了“許仙”和“法海”的愛情,她就是一身“魯迅味兒”的美女作家丁玲。

一、從相遇相知到挑戰“三人行”
1924年,丁玲在北平與同樣是青年作家的胡也頻相遇了。相似的年齡,相同的愛好,他們很快因為有了共同語言而愈發接近。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,若有知己常伴身側,且志趣相投、信仰一致,這該是多么幸運的事情。
然而,就在兩個青年還沒來得及相互表白心跡之時,丁玲的弟弟突然病逝了,丁玲匆匆從北平趕回了湖南老家。
一日,丁玲打開家門,竟然看見胡也頻就站在門外。那一刻,他們無需多言,因為愛情已經來敲門了。

胡也頻就是丁玲的“許仙”,溫潤如玉,彬彬有禮,他們相敬如賓地走過了一段很美好的歲月。1925年,丁玲和胡也頻結合為夫婦。然而,他們的美好生活剛過兩載,“法海”就出現了,這個人就是魯迅的摯友馮雪峰。
丁玲一直崇拜魯迅,因而一度想和胡也頻去日本留學,于是請來了教日文的老師,他就是在北大旁聽自修日文的馮雪峰。
從外在形象來看,馮雪峰沒有胡也頻的英氣,他甚至帶著點鄉土的氣息,起初丁玲對他并沒有特殊的情感。然而,隨著交往的日漸頻繁,丁玲很快就被馮雪峰的才學和風趣所吸引。愛情來得熱烈,還沒來得及設防,心下早已卸下了防備。丁玲甚至大膽地說:“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。”

左手是革命愛侶,右手是靈魂伴侶,選擇哪一邊都是如此不舍。于是,這位思想始終走在時代前沿的美女作家決定挑戰世俗,她選擇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形式:三人行。
丁玲向兩個深愛自己的男人建議,干脆三個人共同生活。在這西湖邊,恰是愛情花開時。大概愛情總會讓人變得卑微,胡也頻和馮雪峰竟然同意共享愛人。
于是,他們租下了兩間房,胡也頻和馮雪峰各一間,他們輪流照顧著心愛的女子。
當愛情需要分享時,除非不愛,否則沒有人可以欣然接受,因為這世間所有情感,只有愛情具有排他性。

最先因為占有欲而感到崩潰的是胡也頻,他選擇去找自己的好友沈從文訴苦。此時的沈從文還沒有遇到自己一生所愛的張兆和,但是他卻深知,只有堅持到底,才會擁有愛情。沈從文給胡也頻的建議是:不要放棄心中所愛。
是啊,只要不放棄,就總有看到希望的可能。胡也頻回到丁玲身邊后,他反而能夠坦然接受丁玲分成兩份的真心。但是,馮雪峰卻無法再繼續下去了。
最終,這段荒唐的“三人行”又回到了原點。它是否曾在胡也頻的生命里留下過傷痕呢?胡也頻犧牲時不過28歲,他在最后的六年中,始終愛著丁玲。
丁玲曾說:“我最紀念的是也頻,最懷念的是雪峰。”
丁玲和馮雪峰的愛情總是不合時宜,他們總是錯過了最好的時間。若干年后,胡也頻犧牲,而馮雪峰成為了她人之夫,縱然有情,這一次他們都無法再向彼此靠近了。
愛情或許沒有先來后到,但它對忠誠度的要求,決定了時間的重要性。

二、善意紀念還是惡意評價?
丁玲的私密情事,源于沈從文寫下的《記丁玲》。在馮雪峰出現之前,是沈從文鼓勵胡也頻追求的丁玲,他成了這對愛侶的見證人。
這期間,沈從文、丁玲和胡也頻這三個窮困潦倒的文學愛好者,共同創辦了紅黑出版社,最終又因缺乏經驗、資金短缺而欠下了債。至此,三人分道揚鑣,卻沒有影響友誼。
1931年,以魯迅為核心的“左聯”成立,丁玲和胡也頻毅然加入其中。沈從文因與魯迅有過誤會,并未加入。或許,信仰的不同,為這段友誼將會出現的裂痕埋下伏筆。

同年,胡也頻被逮捕。得知消息的沈從文幾乎動用了所有關系去營救。然而,胡也頻終是犧牲了,成為了“左聯五烈士”之一。
胡也頻的去世讓丁玲的世界一度陷入黑暗,而沈從文默默承擔起照顧友人遺屬的重任。這期間,為了保護丁玲和胡也頻的孩子不被迫害,沈從文親自將孩子送回鄉下丁玲母親處,交由老人撫養。但是,沈從文因此耽誤了武漢大學的開學時間,最終竟被開除了。
可以說,沈從文為丁玲所做的,都是出自朋友間的情誼。
1933年,丁玲被當時的愛人馮達出賣而入獄。消息放出來時,外界曾一度以為丁玲遭到了迫害,魯迅甚至悲憤地為她寫下了《悼丁君》。此時的沈從文也以為好友犧牲了,于是百感交集之下創作了《記丁玲》,而這部回憶錄也成為了他與丁玲徹底決裂的導火索。

丁玲和沈從文的關系,多半與兩件事的誤會有關。
其一是,丁玲入獄后,馮雪峰曾找到沈從文搭救,沈從文已經動用過所有關系未果,因而拒絕了馮雪峰。丁玲卻認為,這是沈從文的明哲保身,便在晚年曾斥責他是“膽小鬼”。
其二就是,沈從文母親病重,沈從文回家探母時,雖路過丁玲母親家,卻沒有進去探望。當丁母將此事告知女兒后,丁玲心中對沈從文的不滿已經積蓄到了一定程度。
兩件事的疊加,讓丁玲開始刻意地遠離沈從文。沈從文不是沒有察覺,只是他更愿意相信這是丁玲的誤會。

數十年后,1979年時,日本漢學家中島碧送給丁玲一本《記丁玲》,丁玲讀完后勃然大怒。因為沈從文在這本回憶錄中,如實地記下了丁玲的情感私隱。雖然在民國時期可以看做是一個女子的率性,可是在70年代卻是不能被世俗所容忍的行為。至此,丁玲對沈從文的恨意與日俱增。
1980年,時年76歲的丁玲在《詩刊》中炮轟沈從文是“市儈”的“膽小鬼”,指責沈從文的《記丁玲》完全是“胡言亂語”和“胡編亂造”。
面對誤解和埋怨,沈從文從未公開回應過,但他對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到:“丁玲冷不防從背后殺來一刀,狠得可怕!我對他們夫婦已夠朋友了,在他們困難中,總算盡了我能盡的力。”
一段本該可歌可泣的友誼,就這樣在誤解和被誤解中至死未解,這究竟是遺憾還是宿命呢?

三、一生至情至性的女子
瞿秋白對丁玲的評價非常精準,他說:“冰之是飛蛾撲火,非死不止。”
丁玲的一生仿似戲劇一般,面對愛情時,她始終如撲火的飛蛾。曾有人揣測過丁玲和大才子瞿秋白的關系,丁玲卻說但凡當時她想戀愛,必然早就和瞿秋白在一起了。遇見愛情,她從來不曾遲疑。
年少時的丁玲,因為外出求學,見過了廣闊世界的她向家中定下的娃娃親提出了分手。遇見胡也頻和馮雪峰時,她依然大膽地逐愛,她甘愿飛蛾撲火,也要燦爛的愛情,更要永恒的戀人。

丁玲愛胡也頻只因“我并非不喜歡他,但怕他太過愛我”,而她對馮雪峰的卻是“愛得太自然太容易了”。相較之下,丁玲愛馮雪峰更多。但造化弄人,有些感情注定只是短暫的剎那。
胡也頻犧牲后半年,身心俱疲的丁玲陷入了瘋狂的追求者馮達的愛情攻勢中。她或許沒有多愛馮達,但是她需要一個陪伴自己度過黑暗,共享黎明的伴侶。只是,丁玲無論如何也想不到,馮達的愛是這樣不堪一擊。
與馮達同時被捕入獄的丁玲,一口認定這個與自己相伴半年的男人出賣了自己,甚至一度想要自殺。盡管有無奈,也有猜忌,自保的丁玲還是在獄中懷上了“仇人”的孩子。被釋放后,丁玲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,離開馮達,尋找信仰。

丁玲選擇去延安,并在那里結識了小自己13歲的青年演員陳明。丁玲曾說:“如果沒有他,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。”
1942年,38歲的丁玲再次相信了愛情,她與25歲的陳明結為了夫妻。面對外界的質疑和嘲諷,丁玲瀟灑地慰藉愛人:“隨他們說去,讓他們說上幾年,還能說上幾十年?”

從20歲到38歲,丁玲始終如一,她忠于自己的內心,且不懼世俗的飛短流長。因為愛情,向來只關乎兩個人的事情。
最好的愛情當然與年齡無關,它讓每個人可以無懼歲月,只做戀愛中可以撒嬌任性的自己。
1986年,84歲的丁玲拉著陳明的手說:“你再親親我,我是愛你的。我只擔心你,你太苦了。”她至死都愿做個純真的、被寵愛的孩子。
愛情究竟是什么?也許就是:暮色千里,回首,你依然在這里。這便是最好的愛情。